
插圖:郭紅松
幾乎很難有人理解賈立群的這些“怪癖”——一件白大褂、一臺B超機,他的一天從早上七點開始,下班時間定然是無法保證的,經(jīng)常有值班的醫(yī)生看到,前一秒還在電腦前寫講稿,后一刻可能已經(jīng)趕到了診室或手術(shù)臺。
他很少吃午飯,也不怎么喝水,學(xué)生們甚至沒見過他的杯子。
“見過他特別累的時候嗎?”同事和學(xué)生不假思索地擺擺手,“沒見過。”
他脾氣好,檢查時,有患兒家長提出“特殊要求”——“大夫,您能把白大褂脫了嗎?我們家的孩子一看見白的就害怕。”白大褂脫下后,露出里面的羊毛衫,可孩子還是哭個不停。
家長又說:“您那毛衣上還有白色的條塊,您能不能把毛衣也脫了呀?”好在里面還有件襯衣,正好是藍(lán)色的,孩子這才安靜下來,做了檢查。
北京兒童醫(yī)院原副院長穆毅還記得,10年前,一個兩歲的孩子被診斷為惡性腫瘤,賈立群每年都幫他做復(fù)查,10年后,孩子考上了重點中學(xué),那次赴京并不是為了檢查,就是想和“賈爺爺”說聲謝謝,匯報學(xué)習(xí)成績。
每位受益于“賈立群B超”的孩子,都會談起善良二字。他如何冒著風(fēng)險,為患兒解決疾苦,通過仁心仁術(shù)獲得自我實現(xiàn),也讓公眾看到當(dāng)下純粹的醫(yī)者風(fēng)范。
這些不知何時被很多人遺忘的專業(yè)素養(yǎng),敬業(yè)精神,肯為一件事鉆研的態(tài)度,在賈立群這里找到了。
有這樣的前輩是什么感覺?——“一方面你很佩服,感覺他醫(yī)術(shù)真高。另一方面也會覺得自慚形穢,和這么優(yōu)秀的人一起共事,更需要努力啊!”
一次,年輕醫(yī)生參加考試,被問到“闌尾炎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時,第五點實在想不出來,就寫下了“賈立群B超”。
一
賈立群25歲就做了醫(yī)生。
那時候,科里醫(yī)生少,小病人多,空閑時間當(dāng)屬晚上,晚上八九點,他抱著白天B超“沒看明白”的新生兒,回到科里繼續(xù)檢查。周邊安靜,有時,“突然就看明白了。”
他學(xué)的是兒科,但畢業(yè)時卻分到了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定了科室,他有些顧慮:“在這兒,我能干出什么呢?”帶他實習(xí)的老師說:“你可別小瞧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憑一雙眼。練出來了,病人得福,練不出來,病人跟著你一塊遭殃。”
做超聲醫(yī)生的第3年,賈立群練出了“火眼金睛”——那是個還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外院診斷下腹部囊性腫物。門診,賈立群足足看了半個小時,“確實有囊,但沒看到膀胱,腫物會不會是膀胱?”賈立群覺得,自己判斷得沒錯,但需要復(fù)查再證實。門診結(jié)束,他和病房打了招呼,抱著孩子又來到B超室,在屏幕上找證據(jù)。畫面一幀一幀掠過,他發(fā)現(xiàn)了囊下方有小尖狀凸起,這意味著外院診斷為占位性病變是錯的,“這就是脹大的膀胱,一根導(dǎo)尿管就可以解決問題。”
后來,年長的管床醫(yī)生私下問他,你是怎么判斷的?賈立群靦腆地笑笑,說:“我超聲超出來的。”
成為醫(yī)生之前,賈立群的夢想是當(dāng)一名無線電工程師。1974年,他被推薦上了大學(xué),可學(xué)的不是無線電,而是從未接觸過的醫(yī)學(xué)。在北京第二醫(yī)學(xué)院,賈立群成了每天學(xué)習(xí)到最晚的人之一。一次,他把人的頭顱骨借到宿舍,抱著它反復(fù)琢磨。不知不覺睡著了,再睜眼時,他發(fā)現(xiàn)頭顱骨正和自己躺在一個枕頭上。
賈立群也承認(rèn),學(xué)醫(yī)是件苦差事。改行做超聲醫(yī)生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大部分的休息時間用于觀摩手術(shù),將手術(shù)中切下來的標(biāo)本拍成照片,晚上到家與B超圖像對比分析。同事胡艷秀記得,遇到看不懂的疑難病例,賈立群會從頭到尾旁觀外科醫(yī)生做手術(shù),這種堅定支撐著他走過早期的迷惘歲月。“我筆下的每一個字都是有根據(jù)的。”他的手在桌子上點著,很認(rèn)真地說。
如果你見過賈立群最初工作時的狀態(tài),就不難理解這份底氣背后吃的“苦”。北京兒童醫(yī)院腫瘤外科主任王煥民愿意將時間倒推30年,一臺超聲機一間房,賈立群弓著身子寫報告,筆端詳盡地記錄著超聲檢查所見、腫瘤大小,甚至是腫瘤性質(zhì),“什么部位容易長什么樣的腫瘤,賈主任能具體報出腫瘤的病理診斷。”王煥民覺得,這早已超越了超聲科醫(yī)生能力范疇。
隨之而來的,是賈立群在圈內(nèi)的好名聲。不少醫(yī)生遇到“看不明白”的病例,會不約而同地在B超申請單上注明做“賈立群B超”。做完了,有的家長還用手指著B超機問他:“大夫,您做的是‘賈立群牌B超’嗎?”
這被賈立群稱為溫暖的誤會。最瘋狂的時候,他可以連著48小時不睡覺,“如果第三個夜里還有病人,我就堅持不住了。”那次,賈立群熬到了凌晨4點,等病人的間隙,他很快睡著了,頭一耷拉,筆桿就戳到了眼睛。
一次,他在外地開會,回京航班取消。為不影響第二天上班,賈立群改飛石家莊,連夜轉(zhuǎn)坐綠皮火車,一路站到北京。趕到科里,正好早上7點30分,“一宿沒睡覺,但我心情特好,沒遲到,也沒耽誤工作。”那天上午,賈立群一共約了20多位患兒做B超,當(dāng)日下午兩點,才結(jié)束上午病人檢查。
這樣的作息時間,貫穿賈立群的整個從醫(yī)生涯。他承諾,只要患兒需要,24小時,他隨叫隨到。一個休息日,他正理發(fā),剛理了左邊,右邊還沒動,醫(yī)院急診電話來了,賈立群立刻往醫(yī)院趕。最多的一天,他夜里被叫起來19次。
北京兒童醫(yī)院外科手術(shù)室,主刀醫(yī)生王煥民在手術(shù)臺上犯了難,這是一個腹膜后的腫瘤根治術(shù),腹膜后血管和腫瘤緊緊地交纏在一起,深部的地方看不到,下手一摸,無從下刀。
“賈主任呢?”
“快叫賈主任吧!”
午夜12點,電話鈴剛響一聲,賈立群就接了起來。65歲的賈立群一直在家等著沒睡覺,他知道當(dāng)晚手術(shù)很復(fù)雜,也許“用得到”自己。
這樣的默契更多發(fā)生在手術(shù)過程中。一位患有脂肪母細(xì)胞瘤的孩子,第三次手術(shù),在場的醫(yī)生都感到了壓力。術(shù)中,主刀醫(yī)生發(fā)現(xiàn)瘤體邊界不清,無論如何也探查不到。怎么辦?答案還是“賈立群B超”。
手術(shù)床前的王煥民一臉嚴(yán)肅。“把腔鏡再往前伸兩厘米吧。”不露聲色的賈立群,用超聲探頭引導(dǎo)著腔鏡。
兩個小時,腹股溝部的腫瘤被切除干凈。B超探頭向右一轉(zhuǎn),賈立群發(fā)現(xiàn)了新目標(biāo):這是一處新的腫瘤病灶,環(huán)繞包裹著血管,要想完整切下它難極了。
“您先走吧,剩下的我們慢慢弄。”王煥民有些不好意思,掛鐘已指向夜里3點。
“不著急,我陪著你們做。”多年來,賈立群和外科團隊達(dá)成了這樣的默契:手術(shù)不結(jié)束,超聲科醫(yī)生不下(手術(shù))臺。
北京兒童醫(yī)院普通外科主任陳亞軍還記得,一位3歲兒童墜樓重傷,從張家口坐直升機送到北京兒童醫(yī)院。之前一直按常規(guī)治療,直到賈立群發(fā)現(xiàn)患兒一處極隱蔽的消化道穿孔,才及時對癥治療。“一般人判斷不出來,但賈主任B超就能查出來,孩子從樓上掉下來時,把腸子摔破了。”
不足12平方米的小屋子,就是賈立群的診室。一次性床單是剛換的,耦合劑安靜地“站”在B超機旁,摸上去是溫?zé)岬摹W雷印⒁巫由戏胖∨笥炎⒁饬Φ耐婢摺H螒{躺在那兒的孩子有多焦躁,賈立群始終不緊不慢,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有時把家長都看著急了。
“賈主任,您看到底有沒有問題呀?”
來自山西的男孩因偶然咳嗽出血,外院CT回報在胃后方有腫物。
“我在超聲上看不到東西(腫物)。”賈立群拿著探頭在孩子的肚皮上看了又看。
孩子父母還是不放心,又去外院做了經(jīng)食道彩超,報告仍然有腫物。
家長執(zhí)意手術(shù),“開”出來的結(jié)果證實了賈立群的診斷。
二
每位新進科室的年輕人,都曾被賈立群請到辦公室,回答兩個問題——
“為什么選擇這行?”
“你喜歡超聲這行嗎?”
這是國家兒童醫(yī)學(xué)中心,身處金字塔頂尖,競爭是殘酷的。大學(xué)剛畢業(yè),王玉就成了賈立群的學(xué)生。之前,他只在書上、某個講座上,或者電視上見過賈立群。近距離接觸后,王玉發(fā)現(xiàn),賈老師就像父親一樣慈祥。有時,因為患兒數(shù)據(jù)報錯了、論文寫得不深入,他又能體驗到賈老師弓著腰、板著臉,瞬間“發(fā)火”的一刻。
王玉剛進超聲科時,團隊只有5個人,很多人不知道兒童超聲也能做得如此有聲有色。進修的大夫越來越多,“最早科里一年一兩個進修醫(yī)生,現(xiàn)在是一個大夫帶一個兩個。”“如果你說出的診斷結(jié)果,恰巧和他的答案一樣的時候,主任會給你一個特別的眼神,以示贊許。”王玉就曾被這個眼神鼓勵過。
遠(yuǎn)程會診是諸多基層醫(yī)院的選擇。綠色通道應(yīng)運而生,復(fù)雜病例在超聲科的微信群里會診討論,受益的醫(yī)生和小患者愈來愈多。后來發(fā)生的事情,頗具戲劇性,有些被治愈的孩子立志學(xué)醫(yī),他們的人生故事,或許剛剛開始。
這些每年都在上演的故事讓賈立群深深藏在心底,很少被掛在嘴邊。在王玉眼里,賈立群是頂著眾多光環(huán)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夫。檢查前鋪床單,檢查后打印超聲報告,這樣的輔助性工作,有不少大專家往往交給助手來做,而賈立群從來事必躬親。
北京兒童醫(yī)院超聲科主任王曉曼提供了故事的另一面。有一次,賈立群身體不適,問他怎么了,他也不說,堅持到下午把所有患兒B超檢查完。“找我們的外科大夫一看,發(fā)現(xiàn)是急性闌尾炎,切下來的闌尾都壞成一小節(jié)一小節(jié)的。”
同行不理解,甚至在私下問:“賈立群這么拼,圖什么?”
這個問題在2008年2月有了答案。賈立群連續(xù)檢查出幾十例“腎結(jié)石”患兒。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三鹿奶粉#的詞條很快登上了微博熱搜第一名,后面還綴著“沸”字。賈立群憑借對這類患兒超聲檢查經(jīng)驗,和臨床醫(yī)生一起,在短短3小時內(nèi)制定出了“毒奶粉腎結(jié)石”的全國診斷標(biāo)準(zhǔn),并帶領(lǐng)團隊在此后數(shù)月中共篩查3萬多個兒童。
那時,全國很多地方篩查出患有腎結(jié)石的兒童,賈立群忙得整宿整宿沒法睡覺,同事胡艷秀記得,那段時間賈立群幾乎透支了身體,“不是在去機場的路上,就是在去各個醫(yī)院的路上。”
那些質(zhì)問“圖什么”的人,漸漸少了,最后消失了。
同事辛悅一直難忘賈立群那句玩笑話:“你還小,正長身體呢,快去吃飯。”她剛畢業(yè)時,超聲科人手少,上午做完全部病人常常是一點以后,賈立群都會讓年輕大夫去吃飯,自己接待隨時再來的急診。
許多縣市級醫(yī)院的年輕醫(yī)生喜歡聽他講課,講B超技術(shù)、兒科發(fā)展。曾多次聽過他講學(xué)的醫(yī)生王四維說,“不同層級醫(yī)院的醫(yī)生都能從他身上學(xué)到東西,”基層醫(yī)院的醫(yī)生在賈立群身上看到了“兒科超聲醫(yī)生的無限可能性”。
除了有些駝背、白發(fā)多了,賈立群的精神頭似乎比十年前更加豐沛。胡艷秀記得,60歲生日那天,科里同事給賈立群過生日,祝福的卡片密密地插在蛋糕上,幾乎蓋住蛋糕。
同事拿著蘋果問他:“主任,你吃蘋果嗎?”賈立群搖搖頭,“我的牙不能咬,很松了,一直想治,但沒時間。”
有人問他:“主任,您在東北兵團那么多年,后來回去過嗎?”他又搖搖頭:“回京以后就沒去過,沒時間啊。”
時間從來就不是秘密。40余年來,賈立群與“醫(yī)”字為伴,漸漸成長起來的年輕醫(yī)生如今獨當(dāng)一面,傳道授業(yè),念著他的好,也陪著他,從年富力強到雙鬢斑白。
三
終于到了退休年紀(jì),但賈立群的社會頭銜仍不見少,重新平衡工作與生活后,他依然選擇了前者。
從許多生活細(xì)節(jié)來看,賈立群都是失職的。比如妻子生病,他不能陪伴左右;比如兒子的學(xué)習(xí),他幾乎很少過問;比如,他很不“愛惜”自己,闌尾炎穿孔手術(shù)、腰椎間盤突出無法躺著睡覺,寧可拄著拐上班,也不請假休息一天。
講述這些的是妻子,“一輩子都在等他,等他吃飯、等他回家,哪怕等他陪我去趟超市。”碰上一個人在家,賈立群的三餐就是妻子走前準(zhǔn)備的:寫好日期的包子餃子,熱熱就能吃。
生活,也是有趣的。家里冰箱壞了兩次,賈立群找來圖紙自己修,維修的范圍很廣,包括洗衣機、汽車、手機,“但一切都要等他的時間,現(xiàn)在家里的水龍頭還壞著呢。”賈立群特別喜歡汽車,在北京購車限號前一周,他買了輛手動擋轎車,一直開到現(xiàn)在。只是因為工作的緣故,賈立群的活動范圍多為兩點一線(家、醫(yī)院),“家里的汽車年年沒時間打理,九年跑了1萬多公里。”66歲的他輕輕地嘆了口氣。
賈立群“寵”孩子,上學(xué)時,兒子想要一副耳機,很貴,妻子不同意買,賈立群看兒子喜歡,就偷偷買了送他。理由只有一個:彌補愧疚。“生病了,我只有他煮方便面的記憶,或者中午他穿著白大褂,端著從食堂買來的魚香肉絲回家,放下,然后又走了。”
實際上,兒子還有很多尷尬的回憶。“我爸每年春節(jié)都是在醫(yī)院度過的,就因為我們住得近。放假過節(jié)家里聚會,經(jīng)常因為突然來了病人,他參加不了。”
也有脆弱的時候。一次去理發(fā),有個小伙子問他,“你兒子多大,在哪兒上班?”賈立群沒忍住,雙眼里含著欲滴的淚珠。他學(xué)著年輕人的樣子,在聊天軟件上給兒子留言,通常是稀松平常的幾句:“吃了嗎?最近學(xué)習(xí)忙嗎?要注意勞逸結(jié)合。”
“我爸平時話不多,大多都是以行動支持我。”兒子說。
他是節(jié)儉的,賈立群幾乎不打車,一件穿過多年的T恤縫縫補補,又成了他的打底衫;他亦是大方的,每年“七一”醫(yī)院組織黨員愛心捐款至少是一千元,同事重病需要救助一拿就是幾千塊。盡管結(jié)婚超過35年,賈立群的言語間仍有一絲笨拙感,那就是妻子口中的,做丈夫、做父親時“笨笨的”形象。當(dāng)他切換到醫(yī)生時,你又能看到那個有著專業(yè)素養(yǎng)的聰明人。
兒子上小學(xué)時,賈立群接他放學(xué)總是遲到,通常的理由是快下班了,又來了病人。“他上來就跟我道歉,然后說著相同的理由。”兒子在學(xué)校門口一等就是兩個小時,“我和學(xué)校門口小賣部的人熟極了。”印象里的幾次陪伴,是賈立群帶兒子去中關(guān)村攢電腦,他深諳孩子的興趣,“這也直接影響了我現(xiàn)在的工作,與計算機有關(guān)。”
賈立群目光垂下,開始說起了自己的理想:“不漏診、不誤診,讓每個孩子都遠(yuǎn)離疾病困擾。”他指著自己的老花鏡,低頭笑了起來。
仿佛打開了某個開關(guān),賈立群的傾訴欲在這之后變得順暢。窗外是北京的初冬,暖陽和煦,每一陣微風(fēng)拂過樹葉的響聲,像是回應(yīng)著他的心愿。(作者:李琭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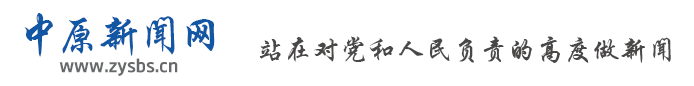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