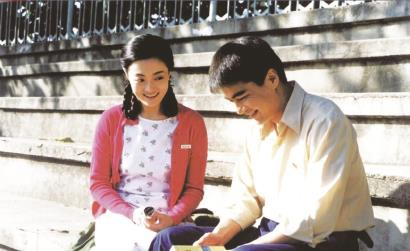
◆ 《一年又一年》用樸實的生活流美學觸發觀眾的審美認同,所采用的“小人物、大時代”敘事策略,也被之后越來越多的現實題材創作沿用

◆ 《浪漫的事》帶有哲學意味的藝術表現,也使作品高于一般意義上充滿糾葛的情感敘事,在對生活與人性的探討中都抵達了較為深刻的程度

◆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經典意義,不僅在于作品對平民生活生動性的獨特發現、對市井人物的鮮活塑造以及精妙勁道的臺詞語言,更在于作品將這一切組合在一起后所激蕩出的多層次藝術效果
近期,沉寂了許久的家庭劇再度成為熒屏上的“主角”之一。《喬家的兒女》在熱播、熱議中收官,話題討論度居高不下。同期的《親愛的爸媽》水花稍小,但亦收獲了一批忠實的觀眾。接著,《婆婆的鐲子》《我家無難事》等劇乘勢播出,還在延續著此番家庭劇熱……
家庭生活劇在過去很長時間里都是國產劇的主流,并且誕生了多部至今被視為經典的作品。它們根植于現實的土壤、反映生活的細末與微妙,凸顯出現實題材影視作品的基本特質。創作者如同用顯微鏡去觀察生活的細節,并如獲至寶地將其融匯到創作中去,以親情為紐帶切入敘事,聚焦于市民家庭的生存境況,描摹普通人的情感與人生軌跡。
時至今日,我們回顧那些已成經典的作品,仍然會被鐫刻其中的濃郁的生活氣息、堅實的生活質感與宏闊的時代變遷所深深打動。它們以生活的光澤感,打開了心靈的開闊地帶,以獨有的真情與溫情敘事始終能夠抵達中國觀眾的內心深處。
希望熒屏上的百姓生活史,能夠繼續被書寫下去。
——編者
家庭生活劇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國產劇的主流。不過近年來,國產家庭劇整體類型創作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家庭劇”與“話題劇”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不清,一些作品甚至用“話題劇”完全置換掉“家庭生活劇”這一傳統的類型概念。曾經的家庭劇用什么打動了觀眾,如今的家庭劇又該如何續寫,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共同的審美特質
用細節、“在場性”與“發現生活”的審美姿態打動觀眾
回顧國產劇歷史上那些出自不同創作者之手、有著不同表現重心的經典家庭生活劇,它們共同的審美特質也隨之顯現。
首先,這些作品在情節推進與情感表現上都是通過極其密實、豐滿的生活細節支撐起來的。這些細節或許瑣屑、庸常甚至困窘,但對生活原生態質感的還原往往會起到舉重若輕的審美效果。沒有濃烈的戲劇沖突,只是讓那說不清、道不明,但卻始終暗潮涌動的情感摩擦與生活細節微妙地推動劇情發展,在一地的雞毛和瓜子殼上,觀眾看見的是熱騰騰的、跳躍著的生命力。
其次,在對大量生活細節的編織中,作品達成了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統一與和諧,并使觀眾獲得一種強烈的“在場性”,即仿佛置身劇中,切近地觀察甚至是直接參與劇中人的日常生活。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當下的一些電視劇作品總令人產生隔膜、夾生之感。因為劇中所描摹的生活景狀從細節上便與觀眾所親身經歷的日常有著較大距離。所以,觀眾根本走不進劇中,作品也無法吸引觀眾。
最后,如果創作者僅僅是“描述生活”的細節,并沒有懷抱著“發現生活”的審美姿態去進行表現,那么仍舊是無意義的形式化處理。世紀之交,生活劇的創作者們摒棄了高高在上的審視姿態,不約而同地以平視的目光去觀照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與精神世界,去發現他們的樸實與可愛,也對他們性格或認知上的缺陷進行同樣客觀的表現,如此才讓他們的生命力與活力在作品中得到相對自由的呈現與釋放。
從家庭生活劇到都市情感劇
城市化進程與消費主義滲透鎖定都市生活劇主導位置
為什么家庭生活劇創作會在世紀之交時形成一股熱潮,并且高質量的作品頻出?除了承接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文壇的新寫實主義創作潮流這一重要原因外,還受到深刻的社會因素影響。
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進程,無疑在短時期內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但這一過程中,并非每個社會階層、群體都能同步從中受益,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與積聚造成各群體之間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加大,陣痛在所難免。作為中國當代最貼近大眾的藝術形式,這一時期的電視劇自覺地將鏡頭對準這些社會問題與社會群體的精神、心態,而家庭生活劇無論是在表現時空、關切對象還是敘事重心上都是最為適恰的題材。
家庭生活劇創作所展現的困窘生活與生存狀態,本身是出于對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的人文關懷。創作者們讓普通人的艱辛生活有機會“被看見”、被理解,從而引起社會對他們的關注,這與消費主義主導下的“被觀看”有著絕對的區別。家庭生活劇中令人尷尬也讓人會心的生活情境,懷柔了觀眾的心,在某種程度上起到緩解社會群體焦慮的效用。觀眾看到時,也許會眉頭舒展地慨嘆一句,“噢,原來我們都一樣!”
就像張大民家留在電視劇史上永遠經典的意象——屋里生長出來的那棵樹。它是深扎在窘迫尷尬與浪漫幸福兩頭的一根中軸,平衡著人生際遇的無常與雀躍,中和著生活的酸甜苦辣。
創作熱潮的形成
對社會問題與社會群體精神、心態的觀照與疏解
近年來,家庭倫理劇向都市情感劇逐漸進行類型遷移,純粹表現市井家庭的生活劇似乎越來越少了。這不僅僅是創作者自身的問題,同樣可以從社會因素中找尋到蹤跡。
更為深入的城市化進程牢牢鎖定了都市生活在電視劇表現重心的主導位置。可是,光鮮亮麗的時尚生活終究不是胡同里、弄堂里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日常,于是一些創作者開始在想象中制造浮夸夢幻的生活表象,期望被觀眾歆慕和仰視,但卻走入了盲目、空洞的誤區。
加之,消費主義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符號消費也隨之成為都市情感劇的一種重要創作表征。CBD寫字樓、高級商場、咖啡廳、酒吧、健身房……這些劇中最常出現的符號不是豐沛人物情感、推動情節發展的生活細節,而是被寄托著一種超越日常情境的消費想象。曾經的生活劇中令人辛酸又會心的細節如若放到其中只會突兀得像個笑話,當前不少電視劇時常有意譏諷的橋段——鳳凰男、鳳凰女們的家長來到大城市后發生的一出出鬧劇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可以理解,當前中國社會愈發多元的話語平臺為群體焦慮找尋到了更多的抒發渠道,并非只能靠某一類特定電視劇題材去排解了。但我們依然希望,接地氣的生活劇能夠依托供它生長的肥沃土壤,再次結下豐碩果實,再像曾經那樣掀起一次熱潮。
《家有九鳳》中有一處情節堪稱妙筆。永遠精神矍鑠的主心骨初老太太終于一天天老去,當老大向她報告九鳳早戀之事并以為她會發怒時,老太太卻一語不發,只是不停地搖頭。老大問:“媽,您為什么一直搖頭?”老太太認真答道:“老八給我買的毛衣領子太高了,我箍得難受。”
也許,家庭生活劇也同樣如此。在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與時代變遷中,不那么光鮮、甚至顯得落伍的家庭生活劇同樣有點力不從心。可誰又能把箍在家庭生活劇脖子上的毛衣領子往下拽拽呢?這還有待于電視劇創作者為我們作出解答。
(本版作者為卞天歌,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博士后)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