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對無知的狂熱崇拜長期存在,這種被稱為反智主義的張力在我們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盤根錯節,這些虛妄和美國式的愚昧大體受到同一種錯誤觀念的滋養,即‘民主便意味著我的無知和你的博學同樣優秀’。”
在著名美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眼中,多年寄生于美國民主制度、自由觀念和草根哲學當中的反智情結,既是美國例外論的典型表征,也是世代美國人輪回體驗的宿命。
該論斷與美國匯聚世界頂級高等教育、科研資源,引領尖端科技研發,把持雄厚知識產品產能的情形構成了令人費解的鮮明反差,彰顯出當今美國社會反理性、反權威、反建制的復合型特點。
越來越荒唐
反智主義因循字面理解,即否認知識和充當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作為一種反常社會現象,此概念往往具象為社會粗俗化、商業掛帥;空洞鼓吹、謠言和陰謀論傳播能力強;碎片化信息取代系統的知識體系等動向。同時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反智主義能夠發展為盛極一時的政治思潮,不僅反對與科學共識相關的政策議題,且大力支持那些旨在壓制、懷疑專家的政客立場和政治運動。
反智主義并非特朗普當政的獨特產物。美國人對政治精英、專業人士的懷疑和敵意,可回溯至18、19世紀的民粹主義大覺醒時期,但直至上世紀中葉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問世,反智主義才真正成為觀察美國社會和政治的經常性鏡頭。
1950年,不喜知識分子的艾森豪威爾擊敗政治家阿德萊·史蒂文森入主白宮,旋即掀起了一場美式“反智狂歡”:反智風潮從社會氛圍上升至政治生態,普羅大眾調侃知識分子,政治精英因為看不慣后者的自以為是、故弄玄虛、好為人師,同樣將矛頭對準后者,理由則是讓他們為所謂的“前朝過失”買單。
這場公開反對和邊緣化知識分子的全民運動,直到釀成麥卡錫主義亂局,且受蘇聯率先發射斯普特尼克系列衛星的雙重刺激后方才迎來反轉。由是可知,對一貫奉行實用主義法則的美國人來說,知識有用論與無用論始終是相對而言的,最終評判標準不看是否精通術業,而取決于能否創造肉眼可見的價值。
這也就不難理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美后,美國社會圍繞反智、反科學甚至反常識為何上演如此之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了。這些堪稱人類奇葩行為大賞的“劇本”概括起來不外乎四種套路。
一是“掩耳盜鈴”型。表現為疫情暴發初期,相當多數民眾否認新冠病毒存在和傳播的真實性,且拒絕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或遵守居家令。更有人鼓吹“陰謀論”,稱病毒肆虐不過是民主黨擾亂特朗普連選連任節奏的伎倆,一旦大選塵埃落定,病毒自會消失;或大肆攻擊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博士為“法西斯主義者”,指責他不該危言聳聽、夸大事實。
二是“以毒攻毒”型。僅2020年1~3月,全美家用消毒劑中毒事件就比2019年同期分別上升了5%、17%、93%,4月23日特朗普發表注射家用消毒液治療新冠肺炎言論后,七日內消毒劑中毒事件比去年4月增長了121%。此外,鑒于短期內疫苗與特效藥難以問世,諸如羥氯喹、地塞米松等無論從藥理還是適用癥均無助于根治新冠肺炎、擅自服用有損健康的藥品,竟然備受推崇。
三是“揭竿而起型”。當短線抗疫宣告失敗,疫情進入膠著期時,反智現象便從公共衛生領域進一步外溢,借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把對政府怠政的怨憤轉化為對歷史過往的暴力清算,拆除雕像、打砸搶等事件層出不窮。
四是“栽贓嫁禍”型。最典型的表述莫過于宣稱新冠病毒絕非自然界產物,而是實驗室秘密研制出的生化武器;還有人把傳染病同5G關聯,指責5G基站輻射危害人體免疫力或擔心病毒通過無線電波快速蔓延全球。
不無夸張地說,部分人已經把蔑視行業權威視為一種全國性的消遣。人們盲目地認為,拒絕專家等同于實現“自治”,因此任由反智主義在公眾意識中日益發酵為反體制、反制度、反歷史、反傳統、反常識的執念。以上種種,造就了后真相時代的美式“愚人”,相較于發泄情感和彰顯個體信念,他們似乎已不再關心專家言論背后的事實,而是不斷重復著無需費力思索的懷疑和抨擊行徑。
美式“愚人”群像
全美各地開展的多項民調指出,與如今這股勢頭強勁的反智風潮密切關聯的,是普通民眾對基本科學知識和社會常識知之甚少或者罔顧事實。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一份報告稱,25%的美國人仍然相信地心說而非日心說;52%不知道恐龍在人類出現前便已絕跡,45%不知道人類文明的出現已有一萬年。另外,只有36%的美國人能完整說出本國政府三個分支機構的名字,超過60%的美國人不知道究竟是哪個政黨控制著眾議院和參議院。
地方調查的數據同樣令人大跌眼鏡。俄克拉荷馬州公共事務委員會委托對公立學校學生進行公民教育調查,發現77%的人不知道喬治·華盛頓是美國第一任總統,只有2.8%的學生能通過本為外籍人士準備的美國公民考試。鳳凰城的戈德華特研究所也做了類似調查,僅3.5%的學生通過了公民考試。
如果將美式“愚人”的群像側寫細化為具體的人口特征,則可管窺另一番圖景。
首先,從靜態人口學指標來看,不同種族對智識、科學領袖和學界的評判存在差異。黑人總體上比白人和其他種族態度更為消極,美國文理科學院相關調查發現,僅28%的黑人對科學家及科學界非常有信心,白人和其他種族此項指標比例分別為43%和45%。但讀寫能力低下者中,美國本土出生的白人比例最高,這也部分解釋了那些非典型總統形象為何能得到白人藍領、農民的支持。從年齡看,反智與年齡正增長相關,35歲以上的各年齡段均有超過50%的人質疑專家的價值和意義。
其次,反智人士在政治光譜上的站位靠右,越保守越反智的現象較為突出。加之近年來共和黨越發保守、民主黨越發自由的政黨極化趨勢顯著,反智群體在共和黨陣營表現突出。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稱,58%的美國共和黨人表示高等教育機構對國家有負面影響,比2015年增長了21個百分點,有65%的保守派堅信“大學誤國”。該中心2020年7月的調查數據表明,85%的民主黨人及其支持者將新冠病毒視為美國公共衛生的主要威脅,但只有46%的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這樣認為。
另外,一些新教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直接反對與氣候變化議題有關的政治行動,而南方的浸信會和福音派則譴責那些科學論證進化論和氣候變化的行為是罪惡所在,并斥責科學家們試圖創造不敬上帝的“新自然異教主義”。在意識形態、政治或宗教上的保守派看來,專家、教授等專業人士及他們的判斷往往聳人聽聞、不值一提。
再次,受教育程度及相應的讀寫認知水平與是否看重智識呈正相關。2018年美國國家科學理事會的調查數據顯示,低于高中學歷的美國人中僅52%相信科學的積極意義大于其負面影響。
從認知水平來看,美國兩極分化明顯,一端匯聚了世界頂尖人才,另一端卻是數量不小的讀寫能力低下者。據國際成人能力評估項目2016年的統計,大約五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讀寫技能堪憂(能力從低到高劃分為1級以下到5級),其中2650萬人處在1級,僅能處理簡單的文字,比如對比兩套旅游特價票的價格、在收視指南上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電視節目,他們無法就兩篇評論的觀點進行歸納比較,更談不上辨識真偽、評判優劣。另外820萬人連1級水平都無法達到,基本處于半文盲狀態。這部分美國人缺乏用智識改寫人生的能力和際遇,也很難識別政治鼓吹或極端思潮的煽動,因此極易充當反智潮流的急先鋒。
最后,反智美國人的地域分布存在一定的規律。生活在東北部和西部的美國人反智傾向較弱,對科學界充滿信心的人分別占47%和46%;中西部和南部則成為滋養反智主義者的沃土,超過半數人口懷疑科學家的可信性。由是形成了“沿海精英”與“真正美國人”的平行存在,前者代表了東西海岸受過高等教育,用知識裝點命運的美國人,后者則代表了銹帶、中西部地區那些自認為被全球化車輪碾壓,被精英階層無視,卻在文化、種族上完整承襲美國底色的美國人。此外,相較于城市人口,生活在農村的美國人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右翼反智主義的論調。
可見,當前美國的確出現了智能化社會和群智退化并存的怪異現象,海量資訊充斥下,人們越來越不能且不愿用嚴格的事實考據和邏輯標準分析思考,蘇格拉底所謂“美德即知識”已很難獲得共識,當然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對知識專家的蓄意無視如何負面作用于當前的科學研究和戰略決策。
但也要看到,公眾的反智情緒其實相當復雜,對科學家行為的期望、對科學專業知識的理解以及對科研機構的信任均不可一概而論,需視特定情況、話題而進行更為深入客觀的討論。
美國病了
反智主義泛起,堪稱美國社會危機的外部化和應激反應,是美國社會陷入病態的征兆之一。究其根源,這種政治上的調侃精英,文化上的貶低知識分子,社會論調上的“讀書無用”以及自我意識上的玩世不恭、奮矜之容、毫無敬畏,系三種變局之果。
一是信息民主化所裹挾的陰暗面。互聯網的高度普及使任何個體在掌握和運用信息方面被賦予了與專業人士不相上下的權利,據此,人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接受信息或接受何種信息,同時沒有哪種價值觀天然凌駕于另一種之上。故而“多數人的智慧”從合法性與分量上壓倒了真知灼見,恣意傳播的謠言和假消息危險地模糊了觀點與事實的邊界,同時也消解了有理有據的抗辯與大放厥詞之間的界限。抨擊專家群體比抨擊專家們的思考“門檻”低得多,于是人們調侃“泰坦尼克就是那些所謂的專家建造的”,言下之意嘲諷“‘磚家’向來不靠譜”。
二是社會議題政治化。無論轉基因食品、氣候變化還是新冠肺炎疫情,這些事關民生、無關政治分歧的社會議題如今都成了兩黨各自圈地、相互爭鋒的“虛擬戰場”。這使得民眾不自覺地充當著黨爭的棋子,越來越無法從兩派不以事實為依據、僅以黨同伐異為目標的說辭中把握真相。由此,同一位專家或同一項科學論斷,被一部分政治精英大加撻伐,卻被另一部分政治精英極力追捧,民眾各自追隨。
三是大眾教育的階層分化。居住隔離和學區制度固化了美國的不平等,原本為社會公平服務的教育如今成為了塑造當下不平等甚至是代際不平等的場域。于是乎,中下層家庭不得不囿于低水平教育和社會資本,他們的子女大多因貧困或復雜的家庭結構而與“美國夢”絕緣,即便少數能夠通過不懈努力改變現狀,但父母能提供的助力相當有限。
教育和居住的長期隔離,使底層百姓產生一種矛盾心態,他們固然看不慣知識分子,不愿子女與父母的生存環境徹底告別,卻又渴望子女通過掌握知識上升為他們心目中的“特權階級”。有鑒于此,大眾認知水平普遍低下,少數精英引領潮流的局面在短期內很難完全改變,而大眾與知識、政治精英的分歧及張力的蓄積卻一刻都沒有停止。
反智美國人“集體出現”,將把美國導向何方?
簡言之,一方面,反智主義長期作為美國政治生態的“認知晴雨表”存在,因此反智主義盛行往往對應著非建制派、非專業人士的起勢和國家內外政策變數及非常規特性增強。
另一方面,反智主義暗含反叛和民粹基因,故而極易挑動美國社會對權勢領導人的盲目崇拜、社會支配傾向、多重偏見和思想匱乏。上述變局折射出美國社會思潮中身份政治和認同政治的回歸,也將進一步刺激美國國內意識形態對立態勢的尖銳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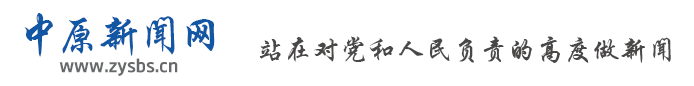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