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日,周建華等4人在廣東省陸豐市人民檢察院領(lǐng)取不起訴決定書。中青報(bào)·中青網(wǎng)記者 魏晞/攝
作者 | 魏 晞
日頭正高,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qū)一處老舊住宅區(qū)的二層樓來了兩個(gè)滿頭大汗的陸豐村民。
那是2019年7月初,他們找到同鄉(xiāng)所在的律所,想找個(gè)收費(fèi)便宜的律師。實(shí)習(xí)律師張文鵬接待了這兩個(gè)村民:年紀(jì)小的周建華脖子上戴了條大金鏈子,“是個(gè)精神小伙”;年長的鄒付敬一只眼看著張文鵬,另一只眼斜視,說話辦事像是位“老江湖”。
他們是來找律師“舉報(bào)”的。這一老一小來自廣東省陸豐市河?xùn)|鎮(zhèn)山蕉坑村,十幾天前,另一個(gè)村民周建銳在家中被帶走了,理由是對(duì)村里的采石場有敲詐勒索行為。他們想請(qǐng)律師為周建銳辯護(hù)。
這次見面沒過多久,鄒付敬、周建華也被帶走了。周建華是在深圳火車站被帶走的,他剛剛結(jié)束了一趟出差。
他們那時(shí)不知道,還有另外4個(gè)同村的村民也陸續(xù)被帶走:年紀(jì)最大的黃君杈是在接送孫子、買完菜后,在深圳的家里被帶走的;陳華波在惠州家里被帶走時(shí),小孩剛出生4天;周玉劍在廣西桂林的印刷紙廠上班時(shí)被帶走;周玉超去北京辦事,結(jié)果在酒店被帶走。
實(shí)習(xí)律師張文鵬怎么也沒想到,未來5年,他和這7個(gè)村民的命運(yùn)扭在了一起。
毀掉的農(nóng)田,回不去的鄉(xiāng)
被捕后,7人被指控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公訴機(jī)關(guān)的指控理由是,村民以無證開采、污染環(huán)境為由,多次到具備合法手續(xù)的陸豐市秋冬聯(lián)泉石場鬧事,敲詐勒索錢財(cái),到各級(jí)有關(guān)部門上訪,影響聯(lián)泉石場的經(jīng)營,使石場蒙受重大經(jīng)濟(jì)損失。
在村民的回憶里,采石場的出現(xiàn)打破了山蕉坑村的平靜。

采石場的礦坑給周邊村民帶來安全隱患。受訪者供圖
從2007年開始,聯(lián)泉石場大量采石,挖山炸石的轟隆聲每天在響,灰塵漫天,飛石能濺到500米外村民的屋子里。每當(dāng)下雨,廢泥、碎石、渣土順著灌溉溝渠,流進(jìn)山腳的農(nóng)田,把農(nóng)田填成沙堆。能耕種的農(nóng)田越來越少了。
陳華波的農(nóng)田恰好在石場下游,是最早被毀掉的農(nóng)田之一。“農(nóng)田是農(nóng)民的根。”盡管他已經(jīng)靠著汽車修理技術(shù)在惠州買了間平房,但他認(rèn)為那只不過是漂泊的暫居地。
村民和采石場的矛盾持續(xù)了十幾年,鎮(zhèn)政府成立了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處理相關(guān)沖突。山蕉坑村幾乎住不下去了,少數(shù)人留下,為采石場打工。有人忍痛賣了祖宅,買了鎮(zhèn)里的房子,多數(shù)人選擇外出打工。
黃君杈回憶,早在20世紀(jì)90年代,山蕉坑村引進(jìn)幾家小規(guī)模的采石場手工作業(yè),他是村子第一個(gè)提出反對(duì)采石場的人,“有了采石場,村子的環(huán)境就廢了”。采石場出現(xiàn)不久,他就決定帶著妻兒到深圳打工。
2007年,聯(lián)泉石場獲得采礦證,開始機(jī)械化作業(yè),山蕉坑村的環(huán)境惡化得更快了。雖然黃君杈人在深圳,但他對(duì)山蕉坑村有感情,堅(jiān)持多年舉報(bào)采石場,但那些舉報(bào)資料寄出后,大多石沉大海。他還回村當(dāng)過村干部,和采石場博弈,為村民爭取了每年7.2萬元的補(bǔ)貼。
2018年5月,在河?xùn)|鎮(zhèn)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的協(xié)調(diào)下,聯(lián)泉石場補(bǔ)給山蕉坑村5個(gè)村民共30萬元的費(fèi)用,鄒付敬、黃君杈、陳華波、周建銳、周玉劍在《調(diào)解協(xié)議書》上簽字按了手印,各自分得12.46萬、4.5萬、4.5萬、4.5萬、4.04萬元。
鄒付敬回憶,當(dāng)時(shí)簽字時(shí),鎮(zhèn)政府的許多工作人員都在現(xiàn)場,他想著拿了這筆錢,順著臺(tái)階下就算了。在此之前,他和采石場對(duì)著干了十幾年,還在維權(quán)時(shí)遇到騙子,被騙了10萬元。
沒過多久,在深圳工作的周建華難得回老家喝了頓喜酒。飯后站在村口抬頭一看發(fā)現(xiàn),“自家的山怎么被采石場挖了大半?”
此前,采石場已經(jīng)兩次越界開采村民的自留山。那是周建華、周建銳、周玉劍、周玉超4個(gè)家庭的自留山。這4戶人家已在外地發(fā)展,周玉超回憶:“之前也越界,但人在外地,想著讓采石場賠點(diǎn)錢長教訓(xùn),別再越界就算了”。
這次越界比前幾次范圍更大,而且只要村民一離開陸豐,采石場就繼續(xù)越界。這讓這4戶人家有點(diǎn)惱火。
4人在自留山上種樹苗,想劃分界線,但采石場的工作人員直接拔掉樹苗,他們只好報(bào)警、向村委會(huì)投訴。為了越界開采的事,在中山市開海鮮檔口的周建銳,不得不每周開車往返于中山和陸豐之間維權(quán)。
周玉超回憶,那時(shí)候他就想,石場的態(tài)度不好,干脆不拿賠償了,直接要求石場關(guān)停,并做復(fù)綠工作。
2018年9月,聯(lián)泉石場因越界開采關(guān)停了。石場前后兩任法定代表人犯非法占用農(nóng)用地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gè)月,并處罰金兩萬元。
周玉超一度以為,他們終于把采石場趕出了村子。沒想到,采石場關(guān)停的大半年后,事情急轉(zhuǎn)直下,先后收過采石場補(bǔ)償?shù)拇迕耜懤m(xù)被捕。
實(shí)習(xí)律師張文鵬了解案情后,有些不平:“石場聲稱有正當(dāng)手續(xù)合法開采,但實(shí)際卻因不斷越界開采、非法占用農(nóng)用地被處罰,最終才被責(zé)令關(guān)停。”那份《調(diào)解協(xié)議書》也寫明,經(jīng)雙方當(dāng)事人自愿同意,共識(shí)一致才訂出協(xié)議,雙方不準(zhǔn)以任何借口提起此事生非。
“周建華一分錢沒拿,只是在自己的自留山維權(quán),反而被公訴機(jī)關(guān)說是無事生非,以強(qiáng)拿硬要等方式滋事。”張文鵬補(bǔ)充。
那時(shí),張文鵬26歲,比周建華大兩歲,正在等待律師協(xié)會(huì)的實(shí)習(xí)面試。他那時(shí)對(duì)什么類型的案子都有興趣,覺得這案子有冤情。“即便村民收了賠償款,公益和私利并不相悖,本來村民就是要保護(hù)賴以生存的土地。”
7個(gè)被捕的村民大多是初中文化,在外地打工。他們之間有些只是打過照面的點(diǎn)頭之交,有些是親戚、鄰居。有個(gè)人在外地安家十幾年,很少回村,以至于侄子都記不清自家叔叔生了幾個(gè)女兒。唯一的相同點(diǎn)是,他們都和采石場有過糾紛。
張文鵬成了村民的辯護(hù)人,他想邀請(qǐng)更多律師加入這個(gè)案件,但家屬實(shí)在掏不出太多錢。
律師劉沛文是張文鵬的朋友。劉沛文回憶,當(dāng)時(shí)他剛剛執(zhí)業(yè),看到張文鵬轉(zhuǎn)來的起訴書,“幾乎是簡單清晰明了的案子,案情不復(fù)雜,一看就是很荒唐、明顯無罪的案子”,激發(fā)了他的興趣。
最初參與的五六個(gè)律師是張文鵬的同學(xué)、好友,大多很年輕,他們懷抱著“無罪”的辯護(hù)目標(biāo),收取較少的費(fèi)用。
回到法律上去
7個(gè)村民被關(guān)在了看守所。陳華波形容,他一度想過死,但是翻案的想法又戰(zhàn)勝了求死的心,“我本身無罪,為什么要認(rèn)罪?”
他想不通:在鎮(zhèn)政府簽的字,又有政府工作人員參與協(xié)商調(diào)解,蓋著鎮(zhèn)政府的公章,為什么會(huì)變成敲詐勒索?
其他6個(gè)人也不約而同地喊冤,在多次審訊中均不認(rèn)罪。周建華表示,“坐完牢,我要出去告到底”。
周玉超在看守所,請(qǐng)律師轉(zhuǎn)告兒子三件事:照顧爺爺奶奶、官司要打下去、要團(tuán)結(jié)。
律師郭會(huì)田看了案情認(rèn)為,這是無罪的案子,也加入辯護(hù)律師團(tuán)隊(duì)。最后,超10位律師加入本案辯護(hù)。
2021年5月,陸豐市人民法院先后對(duì)7人作出一審判決。7人因“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不等,并被追繳犯罪所得返還給聯(lián)泉石場。
一審結(jié)果讓7戶村民和律師們感到失望。
周玉劍被抓后,他的父親去世了、女兒因?yàn)樗陌缸虞z學(xué)了、經(jīng)營十幾年的印刷紙廠也倒閉了。他在看守所突發(fā)腦梗,送去醫(yī)院搶救,昏迷九天九夜,還做了心臟搭橋手術(shù)。
折磨人的,還包括一審判決書中一些村民的說法。那時(shí),山蕉坑村被分成兩派,一派是仍在村子里生活,為采石場工作的村民,希望采石場繼續(xù)經(jīng)營,另一派是外出打工的村民,希望采石場關(guān)停。
“我就要翻案,寧可一天也不減刑”,周建銳在看守所數(shù)著日子,“刑滿是2024年6月18日,我那會(huì)兒30歲出頭,還有機(jī)會(huì)出去翻案、做事業(yè)”。
但這不足以讓7個(gè)家庭把信任完全托付給張文鵬。鄒付敬的兒子鄒貴帆回憶,父親被抓后的一年半時(shí)間里,7個(gè)家庭聯(lián)系得不多,他想找關(guān)系把父親從看守所里“救”出來,還被騙子騙了錢。
一審判決給他提了醒:找關(guān)系行不通,這個(gè)案子還得回到法律上去。
他在深圳長大,決定完全拋棄深圳的生意,回陸豐專心打官司,也慢慢認(rèn)識(shí)了其他6個(gè)家庭的成員,把7個(gè)家庭重新攏在一起。
被逼到絕境,只剩堅(jiān)持
不服一審判決的村民提起上訴。
在庭審上,村民的語言表達(dá)能力有限。郭會(huì)田律師也著急,“村民只會(huì)喊冤,不會(huì)說冤在哪兒,法的依據(jù)在哪兒,不會(huì)搜集證據(jù)”。但他在法庭上,也忍不住說:“如果這個(gè)判決在貴院生效了,我一定陪村民打到底。”
他同情這群樸素的村民,“老百姓不需要太多法律素養(yǎng),被欺負(fù)了,賣房子也要告到底”。慢慢地,為村民辯護(hù)的律師超過10人,都是沖著“無罪”來的。一位法律援助律師也在庭上作無罪辯護(hù)。
張文鵬回憶,一審判決一度讓他感覺辯護(hù)無力,想把案子交給更有名氣更有經(jīng)驗(yàn)的律師,對(duì)方也有興趣接,但為7個(gè)村民辯護(hù),每人要收10萬元,家屬掏不起,只能作罷。于是,作為最早接觸這個(gè)案子的辯護(hù)人,張文鵬只能硬著頭皮繼續(xù)管,“我不管就沒人管了”。
2021年7月,周建華被釋放,從看守所出來的第三天就去深圳找張文鵬,“我要幫其他6人早點(diǎn)出來,里面太難熬了”。
張文鵬說,辦這個(gè)案,對(duì)村民的同情占了一部分,對(duì)法律的信仰占了一部分。他對(duì)家屬說:“這個(gè)案子是被蒙在麻袋里打,我們要讓它暴露在陽光下,讓更多人知道。”
張文鵬和周建華提起公益訴訟的申請(qǐng),請(qǐng)求汕尾市人民檢察院對(duì)當(dāng)?shù)夭宦男蟹ǘ氊?zé),導(dǎo)致石場損壞生態(tài)環(huán)境一事進(jìn)行檢察監(jiān)督。

2021年10月25日,村民用無人機(jī)拍攝山蕉坑村。受訪者供圖
汕尾市人民檢察院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聯(lián)泉石場在2015年、2018年兩次越界開采,被責(zé)令停止開采、做出行政處罰;采礦權(quán)開采范圍是71.25畝,經(jīng)鑒定,聯(lián)泉石場最后采礦總面積是213.45畝,其中林地面積189.6畝;責(zé)令石場關(guān)停后,采礦區(qū)、加工區(qū)、生活區(qū)、礦區(qū)道路復(fù)綠復(fù)墾推進(jìn)緩慢,采礦區(qū)域和周圍生態(tài)一直受到侵害,且礦坑威脅周邊村民的生命安全。
律師們也從7個(gè)村民的卷宗中發(fā)現(xiàn)很多問題,比如一些有利于采石場的村民口供是同一時(shí)間錄的,且有90%很相似,許多口供只蓋了手印沒有簽名。
2022年2月,汕尾中院以“原判事實(shí)不清、證據(jù)不足”為由,將該案發(fā)回重審。
司法的水平線
發(fā)回重審后,一群法官走出法庭,把合議庭開到山蕉坑村里。法官們帶著鏟子走到周玉劍的農(nóng)田里,一鏟子下地,鏟出了碎石頭,還爬到礦坑旁勘驗(yàn)。
只有親臨采石場,才能看到許多細(xì)節(jié):石場關(guān)停數(shù)年后,被沙子覆蓋的農(nóng)田長期無人耕種,長出雜草和小樹,連成一片,變成了荒樹林,還有未清理的碎石壘在農(nóng)田上;站在高處俯瞰采石場,只有一側(cè)山坡復(fù)綠種了樹,其他四分之三的山體被挖空后,露出黃褐色的巖石。
2023年7月3日,在合議庭現(xiàn)場勘驗(yàn)不久,陸豐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刑事判決,鄒付敬、黃君杈、陳華波被不予起訴;另外4個(gè)村民被陸豐市法院認(rèn)定“敲詐勒索”罪名成立,但可免予刑事處罰。
2023年11月,汕尾市中級(jí)人民法院判決陸豐市人民法院向鄒付敬、黃君杈、陳華波支付國家賠償各50多萬元。
劉沛文律師說,3人無罪、4人定罪免罰的判決,在當(dāng)前的刑辯環(huán)境中,已經(jīng)算是比較好的結(jié)果,但7個(gè)家庭堅(jiān)持還要打,打到所有人無罪。
4個(gè)“定罪免罰”的村民再次上訴。為了打“持久戰(zhàn)”,律師們也想辦法給村民們省錢。郭會(huì)田是其中年紀(jì)最大的律師,他主動(dòng)提出要住在村民家里,給家屬省點(diǎn)錢。
幾個(gè)男性律師擠在了村民家里,有人睡床,有人打地鋪,兩人蓋一床被子。郭會(huì)田說,律師們收取了微薄的費(fèi)用,與付出嚴(yán)重不對(duì)等。過去5年,張文鵬在深圳和陸豐間往返了100多趟。
負(fù)責(zé)律師團(tuán)吃住的是這幾戶人家的婦女,她們大多是山蕉坑村人,不會(huì)說普通話,有的也不識(shí)字。周玉超的妻子說,她掏空家底也要堅(jiān)持到丈夫無罪。陳華波被抓時(shí),妻子還在坐月子,40天后就去當(dāng)保潔養(yǎng)家。

律師們?cè)谥芙ㄤJ家商討案情。受訪者供圖
有時(shí)候,張文鵬對(duì)這群山蕉坑村的村民有些不解:“山蕉坑村每戶分到三畝多的地,村民明明在外做生意好好的,居然為了這三畝地回家維權(quán)。”
山蕉坑村屬于山區(qū),不靠海,離縣城較遠(yuǎn),很多村民把這三畝多的田地當(dāng)成命根子。他們?cè)谔锏厣戏N水稻、番薯,自留山種遍松柏。即便最近十幾年,外出務(wù)工的村民變多了,這個(gè)約50戶、350人的小村子就像鳥籠,逢年過節(jié),把外出游子的心收攏到一起。
陳華波說,農(nóng)田被毀后,他連每年農(nóng)忙回家?guī)兔κ盏竟鹊臋C(jī)會(huì)都沒有了,“我將來是要葬在山蕉坑的”。
張文鵬說,希望“這個(gè)案子成為裁判案例,以后當(dāng)農(nóng)村環(huán)境嚴(yán)重被毀,村民要錢不再犯法”。
冤獄的痕跡
2024年3月25日,陸豐市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書》:陸豐市人民檢察院認(rèn)為本案證據(jù)不足,向法院撤回對(duì)周建銳四人的起訴,陸豐市人民法院準(zhǔn)予撤回起訴。
村民和律師團(tuán)的堅(jiān)持有了結(jié)果:7人均無罪。
“這類案子中,極少數(shù)能有全部無罪的結(jié)果,”律師郭會(huì)田說,“村民的心太齊了。”
實(shí)習(xí)律師張文鵬張羅著在深圳辦了場慶功宴。鄒付敬在飯桌上念了幾首詩,是他在看守所時(shí)寫的。申請(qǐng)國家賠償之前,他大手一揮,流露出幾分豪氣,表示寧可不要國家賠償,要一只眼睛。進(jìn)了看守所以后,他的瞳孔移位和知覺性內(nèi)斜更嚴(yán)重了。
對(duì)于這7個(gè)村民來說,恢復(fù)生活還需要一些力氣。
經(jīng)歷了腦梗、心臟搭橋手術(shù)的周玉劍,釋放后去應(yīng)聘片皮鴨的工作,被老板婉拒了。他總是低著頭,跟著人群走在最后,“我后面的人生,沒有太多計(jì)劃了”。
周玉超原先在廣東省普寧市做印刷紙生意,雇了十幾個(gè)工人,年景好時(shí)能賺小百萬。從看守所釋放后,印刷紙廠已經(jīng)倒閉了,56歲的周玉超回到河?xùn)|鎮(zhèn),當(dāng)建筑小工抬水泥。后來,他換了一份不用日曬的工作:在市場賣豬肉,每月能賺2000元。
2024年4月2日,陸豐市人民檢察院通知周建華等4人,領(lǐng)取不起訴決定書,這意味著,4人的無罪程序走完了最后一步。
周建華戴回了初見張文鵬時(shí)的大金鏈子。領(lǐng)完決定書后,他第一時(shí)間趕回佛山賣海鮮,他頂著黑眼圈說:“下午去(陸豐)檢察院(領(lǐng)取不起訴決定書),晚上還要回佛山接貨。”
周玉超當(dāng)天凌晨5點(diǎn)就去賣豬肉了,下午才趕回家,他急匆匆地洗了個(gè)澡,換了身顏色鮮艷的新衣服,蹲在天井旁刷皮鞋——殺豬的豬油滴到皮鞋上了。
周玉超踩著擦得锃亮的皮鞋走出家門去檢察院。沒走兩步,他說:“等了四五年,終于等到今天的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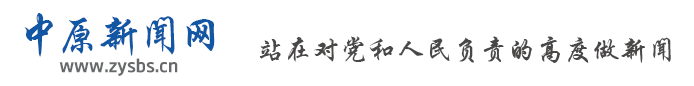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


